无意第一次就喜欢的人再次遇见还是会心潮澎湃中瞥见历史的一角
最佳回答
“第一次就喜欢的人再次遇见还是会心潮澎湃”无意第一次就喜欢的人再次遇见还是会心潮澎湃中瞥见历史的一角
王锐的书籍和手稿被发现时,在一辆废品站三轮车上。受访者供图 江苏常州武进区档案馆提供的人物志,有王锐的简介。受访者供图 一本俄文书扉页上,有王锐的签名。受访者供图 最初只是一位南京市民,瞥到了一本出现在废品站的莎士比亚著作。接着,她翻看了“莎士比亚”旁边的更多书、词典和笔记,发现了一个名字。随着她把这次意外“相遇”发到网络上,一位老科研工作者的人生引发了全网关注。 数百万人为这个陌生的名字驻足停留,他们想知道与之相关的一切,也想起了自己的祖辈、家人。 “这些字拉着我的头发” 这是一次偶遇。 10月8日傍晚,生活在江苏南京的冯源去买菜,经过废品站时,注意到装载废品的三轮车上有一本红色封面的莎士比亚作品。 它和很多书一起,待在两个敞开的大口袋里。冯源停步仔细翻找,发现里面还有医学期刊、医学工具书、画册和很多词典,其中有1953年出版的《俄华大辞典》。书都很陈旧,扉页上没有标注主人的名字。 翻着翻着,冯源的动作开始变得越来越小心――她翻到几页字体好看的手稿,深蓝色墨水记载着与药物有关的内容。冯源看不懂,但她觉得手稿写得很用心,堆在那里,太可怜了。 “这些字拉着我的头发。”她说,虽然平时从不淘旧书,但冯源决定买下它们,甚至来不及去想买回去如何处理。 装书的口袋脏了,有的书还带着水渍。冯源在书堆里挑选了十几本,以及那些“字体好看”的大部分手稿。 冯源记得,当时她问过废品站老板:“要是人家后悔了来找这些书怎么办?” “人都走了,谁来找。”老板回答。 “可能是某个人的遗物。”冯源想,“如果这个人还在世,手稿和书应该不会出现在这里。”她没有害怕,却感到一阵惭愧和心虚,似乎自己用不当手段把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了。她付了60元,没有与老板过多交谈,很快把那些书本笔记带走。 回到家,冯源给它们掸了掸灰尘,喷了些防书虱的药,就放到阳台晒太阳。10天后,她出差回来,开始仔细翻阅,一个陌生人的信息逐渐在她面前展开。 一张1983年江苏省卫生厅颁发的工作证,让冯源确信,这些书籍和手稿的主人叫王锐,出生于1928年,女性,江苏常州武进人。20世纪80年代,她在南京药物研究所工作,专业从事药物合成。王锐学习过俄英日三门外语――那时冯源的父母都还没有出生。 在印制了南京医科大学、南京药物研究所等单位名称的稿纸上,王锐用汉字、拼音、英文记录了关于灭螺药物的研究内容,这些内容都与血吸虫病防治有关。 一本俄文书的扉页上有用繁体手写的“王锐购于哈医大,1953.4.7”,左边有几笔烟花涂鸦,右边画了一组化学结构图示。冯源几乎能够想到,25岁的王锐雀跃地用钢笔在一本新书上描画。 猜测着那个模糊的身影,冯源有好多问题想问。 “谁教你俄文?你去过苏联吗?你对什么最感兴趣?” “你小时候的生活是什么样的?你青年时代经历了什么?” “时代在变,你的研究方向一直没有改变,你为什么这么坚定?” …… “我意识到,我捧着的是一个陌生人此生的证据。”冯源在社交平台上记录了这次奇遇,引发网友关注,许多人为这场跨越时空的相遇动容。一些网友行动起来,开始寻找更多关于王锐的信息。 拼凑零碎信息,寻找她的痕迹 芬兰有一部纪录片《冰山的阴影》,导演通过一箱在跳蚤市场发现的8毫米胶卷,还原一个陌生男人的一生。胶卷留存了世界各地的风景,以及男人的旅程与探索,最终拼凑出他平凡却丰富的人生经历。 网友们聊起了这部纪录片,期待冯源发现的书籍和手稿也能找出更多王锐的故事,然而结果令人失望。 除了废品站老板的一句“人都走了”,目前还没有明确信息表明王锐的现状,书籍和手稿如何出现在废品站,王锐是否也居住在此地,这些问题未解。 许多媒体记者联系冯源,也加入到寻找王锐的人群中。南京药物研究所(现更名为“江苏省药物研究所”)答复称王锐已经退休多年,现任副所长也不记得她。 在学术期刊网站中,能检索到的王锐发表的论文,最早的是1960年发表在《南药译丛》(现更名为《药学进展》)上的论文。 生活在互联网时代的冯源,对搜索不出一个人的更多信息感到困惑。网友则热情高涨,将这个故事送上了各种网络热搜榜单。 但直到本报道刊发,还没有直接认识王锐的人联系冯源。“她还在学校任教过,按理说应该会有学生能记住她吧。”冯源说,有人听说王老师很谦和、很有大家风范,但别的也不知道了。 10月21日,在网友的建议下,冯源将其中一些旧书和全部手稿,捐赠给王锐家乡江苏常州武进区的档案馆,工作人员发来馆内收录的王锐的人物志书页,为故事增添了更多信息。 武进区档案馆工作人员告诉中青报・中青网记者,这是该馆第一次收到王锐本人的手稿和书籍,目前材料还在整理过程当中,感谢年轻人对科技工作精神传承的关注,希望广大网友今后能够为档案馆提供更多线索。 故事不完整,也不妨碍网友表达对王锐的敬佩,通过拼凑零碎的信息,人们认识了一位一生致力于消灭血吸虫病的科研工作者。 血吸虫曾是一代人的梦魇。新中国成立之初,长江流域及以南13个省份遭血吸虫病侵袭,近1亿人的健康受到威胁。儿童患病影响发育,妇女得病多不生育。1956年,毛泽东发出“全党动员,全民动员,消灭血吸虫病”的号召。1952年毕业于南京药学院的王锐,和许多科研工作者一起,投身于这项任务。几年后,抗击血吸虫病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显著的成效。 王锐的书籍和手稿,引发很多人对血吸虫病的回忆。有人回忆,小时候在武汉长江边游泳,听长辈说,过去长江里有可怕的“血吸虫”,感染之后会生“大肚子病”,非常痛苦。 当时,我国主要流行的是日本血吸虫病,钉螺是日本血吸虫的唯一中间宿主。使用灭螺药是防治血吸虫病的重点方式,这在王锐身处的年代,还是比较前沿的防治理念。 在王锐的手稿中,灭螺药物重点出现。王锐记录道,理想的灭螺药物具备安全、副作用小、稳定、对非目标生物无害、价格便宜的优点,既杀螺又杀螺卵,用量小便于运输。 武进区档案馆人物志记载,20世纪80年代,王锐开始从事灭螺药的研究,其中对药物吡喹酮的研究,于1980年获江苏省科技成果奖、卫生部乙级科研奖,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。1992年她被国务院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。 她还以为看到的是自己的外公 许多网友称赞了冯源买下书籍和手稿并捐赠的行为,大多数人认为,这一举动让一名重要的科研工作者被更多人认识。有人也因此愧疚,从未好好了解自己的长辈;有人开始思考,逝去的长辈有没有留下什么资料。 老家在新疆的李梓艺起初浏览冯源社交媒体的笔记,以为看到了外公的遗物。她记得,外公也有许多出版日期久远的俄语书籍资料,什么时候学的,怎么学的,她不知道。李梓艺尊敬王锐,也对外公感到愧疚:“我从未仔细了解过他的生平。” 听母亲讲述,老人1942年出生,家里是从东北去的新疆喀什。外公年轻时曾是一名教师,作为当地唯一会说维吾尔语的汉族人,当地人有什么事都会找外公帮忙。班上有些维吾尔族孩子,书读到一定年纪就休学回家种地,这位教师挨个到他们家中劝学,还提供资助。有几个复学的孩子不情愿,他常常得去把人领到学校,揪着衣服让他们学。 李梓艺小时候不理解,好多学生以前明明很害怕外公,但是他们长大以后居然会回来看望他。“他骄傲地炫耀,说自己教过的每个学生都是好孩子。” 李梓艺读大学时,只在寒暑假回新疆老家,当外公聊起民族大义与家国情怀的话题,她总觉得没意思。随着年龄渐长,她开始认真听外公讲述的往事,“可是我回去得少了,现在我想知道更多,外公已经在2022年去世了”。 00后大学生何思景看到王锐的书籍和手稿不知缘何散落在废品站后,想起了外公去世后他那些被烧掉的歌曲创作手稿。 何思景的外公年轻时当过兵,退伍后在家乡云南宣威的磷肥厂工作,他自学了二胡和电子琴,并且自创歌曲、自弹自唱。退休后他加入老年合唱团,写歌,为朋友写祝寿歌,写赞美祖国、赞美解放军的歌,积攒下厚厚的一摞歌曲手稿。 何思景说,外公没有非常专业的乐理知识,创作的歌曲质量不算高,都是朗朗上口的简单词曲,但她很喜欢,最喜欢的是一首外公写给年幼的女儿――也就是她母亲的儿歌。“几十年来,他唱给我妈妈听,又唱给我听。”家里人都对音乐不感兴趣,只有何思景爱听外公唱歌。 然而,老人在去世前五六年,经常生病,精神也渐渐变差,记不清琴谱,手发抖,弹琴变得不流畅。有时外婆觉得吵,让他别弹,外公也不会很生气,只是小声嘟囔几声表达抗议:“你们都不懂。”后来他不弹了,那些歌曲手稿被尘封起来。 不再弹琴,何思景外公的生活变得很简单,慢慢地,他也不再去合唱团,因为乐团里的老朋友逐个去世了。何思景记得,晚年的外公每天早晚都在看电视,下午坐在院子里晒太阳睡觉,精神好一点的时候会去街口看人下象棋。 2022年5月,老人去世,因为新冠疫情,在外上大学的何思景没能回家。问起外公的遗物和手稿的下落,母亲说在遗体火化时一起烧了,二胡、电子琴和那些手稿,全部都烧了,只留下一块手表给何思景。 “家人说按照风俗,就是要把东西都烧掉,如果留在家里,逝者的灵魂会不愿意离开,一直飘荡在这里。”在何思景看来,那些手稿都是他人生轨迹的缩影,最后都随烟消散了。 后来,何思景能感觉到家人的后悔,“妈妈说应该留下一些”。她母亲换了个角度安慰自己:把父亲最喜欢的东西烧给他,它们能在另外一个世界陪着他,这么想就没有那么难过了。 在冯源发布笔记的评论区,有个别网友指责说,是后代把王锐的物品卖掉。“我最害怕的就是误伤到人,我觉得其中肯定有隐情。希望大家能去保护,而不是攻击。”冯源删除了一些评论,她很庆幸没看到更过分的话。 网友魏天晴回忆,她的外婆生前是一名医生,去世时留下了一箱遗物,其中有老人一生的心血――好多本手写的药方,却在搬家时被人偷走,不知去向。“物品流落,有很多种可能性,不一定是被卖掉。”魏天晴猜想。 她认为,有些物品出现在旧货市场,说明还有变现的价值,能被人看到,而很多没有变现价值的物品,最后一定都默默消失了。 瞥见历史的一角 冯源用“缘分”概括这次相遇,她说自己不算念旧,但对书和日记除外。她手写并保存了13年的日记,每天不写完日记睡不着觉,想不起的事会随时在日记里查找。 “平常在路上和一些人偶遇,我会猜想他要去做什么?看到有人和我一样坐在湖边发呆,我会想他这会儿的感受是不是跟我一样?”那本出现在废品站的红色封面莎士比亚作品,引起她对一个陌生人的好奇心。 有人在冯源的记叙里读到伤感。“连这么优秀的人都被人遗忘,那我们这些普通人呢?” 家在广州的陈晓霖小时候以为,大部分老人都有写自传的习惯。她的外公出生在1929年,是新中国的第一批大学生,学习铁路桥隧专业,毕业之后进入铁路系统,在职40年间,他在湖北、福建、江西三省做铁路桥梁设计工程师。 陈晓霖对外公的记忆是他每天“写书”。2004-2008年期间,老人手写了约10万字的回忆录,内容包括他的童年、求学、从业、成家等经历。后来她觉得,外公除了想给后人留下纪念,还是在完成他兄长生前撰写家族史的愿望。 那本回忆录将中国近现代史以个体视角呈现在陈晓霖眼前。外公的童年经历战争炮火,青年时期在民国的混乱局势中几度中断学业,大学毕业后成为国家重工业的一员。 “每个人在时代浪潮中有不同的境遇,我虽然完全不认识他们(回忆录里的长辈),但还是有瞥到历史一角的震撼。”陈晓霖说。 近年来,给老人代写回忆录的小众行业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。 “普通人的一生也值得被记录”,兼职从事代写回忆录一年多的青梅,把这句话当作信条,她和网友一样,对王锐老人的故事感慨:“如果不是博主发现,可能也就没有人知道她的过去了。” 2022年年底,由于身边一些老人猝不及防地逝去,做过多年出版编辑的青梅想着,或许可以尝试帮人写回忆录。她在微信朋友圈发布了信息,接到一位朋友的委托,开启了第一次代写,到现在已为近10位老人撰写了回忆录。 青梅说,一般是老人的子女晚辈前来请求代写,老人本人则很少,许多人觉得,自己一生普普通通,按部就班,没有什么好写的。 写回忆录前,青梅需要通过当面和电话访谈,与老人多次交流,积累写作素材。有人会向她坦陈苦痛、委屈和失败的经验,有人则倾向于呈现完美的形象。 在青梅看来,代写回忆录在某种意义上是给老人提供情绪价值。“有的老人,在生活当中没有办法去讲,也没有人倾听,借这个机会去表达,因为他们知道回忆录最后会被子女看到。”青梅认为,这是人工智能暂时替代不了人类的地方。 不过,青梅明白,写出来的回忆录,可能只有老人和青梅自己会逐字逐句地阅读,老人的亲友未必能从头到尾看完。对他们来说,重要的是有东西留下来。 “这是普通人的人生,真正仔细读的人不多。”青梅感叹。 冯源说,如果她不想留着日记了,会烧掉,书籍捐赠出去。她喜欢看自然类纪录片,恢弘的场面常常让她想到世界之大,个体之渺小。“我现在能感受、能说话、能记录,就已经很好了。” (应采访对象要求,冯源、魏天晴、青梅为化名) 中青报・中青网见习记者 戴纳 李怡蒙 记者 秦珍子 来源:中国青年报
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
热门排行
- 评论
- 关注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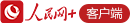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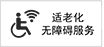

 第一时间为您推送权威资讯
第一时间为您推送权威资讯
 报道全球 传播中国
报道全球 传播中国
 关注人民网,传播正能量
关注人民网,传播正能量